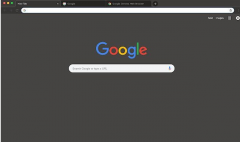过散渡河桥向北,一路爬坡,车像负重的老牛,喘着粗气,急转弯,之字坡一个接着一个,人和车一样累到极点时,突觉眼前视觉开阔,回望来路,山连坡走,便知到了山顶。路稍平,有一村在路旁散开,一溜出去,仿佛盆栽的几枝兰花草,清幽中透出几分秀雅来。秀雅的同时,那名儿也别致,尽管取的也是随景赋形,少了几许别致,但真叫出来,还是满蕴古文化气韵——椿树岘。在椿树和其他苍松翠柏的簇拥掩映下,罗家庙以轩昂之势极天而立,那些飞檐斗拱,特别是那卓异不群的傲岸劲儿,在将宗教的神圣推向一种极致时,也将一种震撼巍峨于天地之间。
出甘谷县城过渭河大桥北上,入散渡河川台地,一路平缓,没什么险峻处;沿姚杨公路,明显是西行;惟有走甘谷到大庄这条道,让人心里觉着,事实上也是一路朝北,挺神圣的。我对勘舆,对风水有点兴趣,但说到具体,又实在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每到八里湾,每到椿树岘,仰望罗家庙巍峨华贵的牌坊,都让人有一种甘谷“北大门”的感觉。因着这种感觉,每次走这条线,总让人觉出几分庄严和亲切来,八里湾,无论从版图、风土人情,还是文化象征意义上来说,特多亲和力、感召力,更有一种横空出世的傲岸,构成八里湾独特的文化景观。
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极富象征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椿树被认为是长寿和顽强生命的象征,是能够和龙风、麒麟、龟这些神圣之物相提并论的。比起龙风、麒麟这些神奇得有点缥缈的“动物”,椿所具有的植物意义却那么苍郁地挺立在我们视线所及的地方。
八里湾的版图意义更像是一棵巨椿躺在地上的投影,一梁直上,村庄散落两旁的八里湾乡酷似一棵千年大椿的造型。民风像碧叶一样苍绿而明莹,传统像树干一样遒劲而苍老。在八里湾,像山风一样扑打我,让我的心灵得以一次又一次震撼的,是那种来自悠久岁月深处的文化信息。1994年夏天,我曾专程去马家岘村龙凤寺考察。论规模,不大;论体制,甚至不全,对于村民言谈举止中隐含的对于悠久历史的回问我表现出同样的茫然。盘桓在龙凤寺,我更多感到的是一种氛围,一种似乎是从历史的地心深处荡起的氤氲。禁不住朋友的托咐,我曾写了关于龙凤寺的,也在几个报刊发表,文中不乏溢美之词,但那种对于表象的叙述或赞叹都是苍白的,龙凤寺给我的是一种感悟,是一种文化的独特和黄土般的质朴,可惜我很难用恰切的文字表现出来,只能归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奈。去年,著名学者雍际春教授来信了解有关崆峒寺的情况,茫然像雾水一样再次困扰着我,对一座湮灭已久的寺庙,还有一些学者能记着它,去怀念它,是幸?还是不幸?文化是脆薄的,就像一个陶罐,一旦从我们的指缝间滑落,落地开花,便不再是陶罐,而是几千年无法粘合的历史,当一只又一只这样的陶罐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指缝间滑落时,历史的迷雾便山岚一样升起,缭绕在我们的意识深处。
八里湾是梗硬的,那道山梁托起的深沟大涧,以及在这些深沟大涧中演绎和派生的故事,似乎都有一种注解的意义。在八里湾贫瘠干枯的悬崖边,倒处都是椿树,耐得住贫瘠,耐得住孤独,耐得住山风的巨掌一次次推下悬崖的威胁,但一次次,一年年它都挺立着,孤独而平心静气地挺立着。这大椿的形象,常使我联想到这条梁上代代衍生的八里湾人,质朴而坚强。椿树不是珍稀物种,更不是名贵花木,但它坚挺、硬直、宁折不弯,常用来作屋梁和檩子。在铁钉还是“王谢堂前燕”时,椿木的木錾完全充当了铁钉的角色,一但认定位置,不腐、不蚀、更不动。这种品格,这种生于泥土的品格自然会影响到她的子民。徘徊在八里湾梁顶,一任山风掠过我零乱如蓬的发际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古人马河图,一个是今人赵明鼎。从八里湾焦灼的山坡上走出来的马河图,在清光绪戊子科中举后,选择了秦州、阶州的教谕生涯,在清末乱世,这种选择是主动,被动,还是无可奈何,现在已无法说个清楚,“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举人马河图的黄鹤楼更多的蕴藏在他山林一样丰茂的书画中,那种飘逸和雅致,那种在点划之间流露或无法掩饰的正直文人的梗硬,常使我得以透过淋漓的墨迹和苍黄的宣纸和举人对话,感触那种大椿一样的平凡质朴,一样的凛然正气。而作古的今人赵明鼎,在用一双长了飞毛的脚溅起八里湾梁顶一路风尘,光着脚丫跑成通渭县万米冠军,陇南田径运动会5000米、10000米、15000米冠军,跑进兰州大学体育系,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后,继续着他的冠军征程,从兰州市3000米冠军,西北军区全军运动会1500米、5000米、10000米冠军,全军首届运动会5000米、10000米冠军,从解放前跑到解放后,冠军依旧,惟一不同的是光脚丫有了鞋的管束。此后,先是由总政治部选拔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建军节运动会,并任分队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设宴饯行,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捷克斯洛伐克领袖哥特瓦尔德亲切接见,和当时世界万米冠军、长跑名将扎托匹克同场比赛,获哥特瓦尔德银质像章。回国后,继续获西北军区、全军运动会5000米、10000米冠军,赵明鼎完全可以继续他的巅峰时刻,走一条更光明的路,但在1958年一个普遍的日子,不普通的赵明鼎却选择了和八里湾土脉相连的通渭中学,当了一名平凡的中学体育教师。如果说对于马河图的选择我们无法说清的话,赵明鼎用他的一生一再表明着这样两个词:主动和不悔。这种在泥土中盛开的生命之花和理想之花,就像八里湾山坡上的苦菜花,平凡、坚贞,以默默开放显示着存在的纯朴和线年,我和王海成等三人去八里湾乡尚坪村,进沟前,我们将自行车寄放在梁顶一户人院里,主人是两个年迈的老人,看我们急着下山,老人说晚上回来一定家里吃饭。很顺利,到结束时,热情的女主人的饭菜已上桌了。吃完饭,打着饱嗝,踏着暮色走到山顶取车子时,年迈的老人早在门口等我们了。老人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我发现,为了等我们一道吃饭,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吃。老人说过回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但久困城市,久为尘嚣所累的我,压根只把老人的话当作一种客套,当冒尖的几碗饭端上桌时,我才感到什么叫真,什么叫情,什么叫庸俗和市侩了。尽管我已经吃得很饱,但那次,那碗饭,是我吃过的饭中最香的一碗。
八里湾属于黄土高原地貌,那种绵绵的黄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只要有水,哪怕是很少的水,她们就会生长,就会贡献,就会倾其所能地付出。在八里湾,我一次又一次感到这种黄土般绵绵如酥的亲和力,这是一种真情和美德的自然流露,是平凡中演绎的纯洁、纯粹和纯贞。
八里湾乡名源于乡政府处在一新月状八里大湾的中部,这种浑阔和新月般的柔美,构成了八里湾的又一全新景观。沿梁而上是绿带般缠绕的树林,苍郁,旺茂,山花野果杂处其间,显红显绿,俨然一幅幅水彩画似的。
从高中课本上学毛泽东主席《沁园春·雪》,到大学毕业后站在讲台上再给学生讲这首气势磅礴的千古绝唱,自以为也差不多了。1992年隆冬,一夜大雪之后,清晨,当我走出八里湾乡政府,站在中心小学门口向西眺望时,醍醐灌顶般,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主席笔下“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天才比喻,纸上得来终觉浅,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高声朗诵这首千古绝唱时,那种豪迈、豪壮、豪放,那种雄视百代的壮怀,让人心灵为之震撼。八里湾素雪覆盖的山原,在让我真正读懂一首诗的同时,更给了我一种来自原野的感召,那种生命的激情,是如何冲破坚硬的冻土,绽放出革命理想主义的花朵。
大雪覆盖的地方,几年后有一个人唱着“关关睢鸠”,撩开“蒹葭苍苍”,从《诗经》中走来,他就是八里湾冯坡村走出去的著名学者、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冯浩菲教授。又是一教师,一个马河图、赵明鼎的传人,就在他用学者的冷静和游子的热情将八里湾这个普通的名子一再写入砖头一样的煌煌巨著时,历史不得不顾盼生情,为一种文化的质朴和深沉所感动。
新月悬在大椿的梢端,这是感性之于理性的对话,是平凡之于深沉的抒情,当这一景致以构图的优美成为画框中的风景,成为快门瞬息千年的定格时,八里湾正以新月和大椿优美刚劲的姿势,写下一首首新的《诗经》,新的《沁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