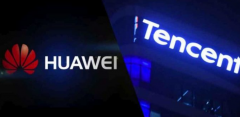此后该公司火速辟谣。根据中基协官网数据,2024年运舟私募的管理规模已经回落至50亿~100亿元,当初和周应波一起“奔私”的另一位公募名将陆文俊也选择了“单飞”。
据私募排排网和好买基金网,目前运舟私募旗下能查询到业绩的产品仅有运舟致远1号1期,基金经理就是周应波本人。这只产品成立于2023年12月5日,阶段收益如下:
由于产品成立时间并不长,因此从近一年、成立以来的收益来看,还是可以排进同类产品前50%;但如果看近半年等短期业绩,几乎就是在同类后30%的水平。相比之下,周应波在公募基金的代表作中欧时代先锋、中欧明睿新常态等,任职回报在同类产品均排在数一数二的位置。要比较双方业绩,或许还得拉长观察周期,但在今年A股市场持续回暖的背景下,运舟致远1号1期交出的成绩单只能算是平平。
还有曾被誉为“创业板一哥”的几年来,该机构旗下产品以“大开大合”出名,单周净值涨跌幅超过二十个百分点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根据Wind数据,由任泽松管理的3只产品任职以来亏损都超过30%,尤其这三只产品从2022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亏损幅度都令人咋舌,也引发了业内对于他本人依赖高成长赛道策略的质疑。
还有部分机构从数十亿元甚至更大规模逐步下滑,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走到门庭冷落、销声匿迹。
今年3月,华安基金原总经理童威也曾在2021年创立另外,去年8月,泓德基金原副总经理、知名基金经理邬传雁正式“奔私”,成立了深圳市一诺私募。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根据中基协官网,目前一诺私募旗下一共成立了5只私募基金产品,其中仅有1只是今年成立的,公司管理总规模在0~5亿元,属于稳扎稳打但步子走得比较慢的代表。
事实上,私募基金赛道竞争也是相当激烈。除了星石投资、淡水泉等早期的“公奔私”机构经过近20年牛熊历练,凭借长期累计的正收益坐稳百亿规模,大部分转战私募赛道的基金经理和机构情况其实都和一诺私募相似。
潮起潮落,人来人往,才是这个行业的常态。而在这种分化背后,“平台依赖度”是关键变量。
双向流动:行业生态重构中的平衡之道
在刘岩看来,“奔私”基金经理在公募时期的高收益中,平台红利的贡献比例因个体差异和市场环境而异,综合行业特征与典型案例来看平台红利对其业绩的贡献率可能在30%左右。
他拆解了平台红利的几大构成:在投研覆盖广度方面,公募基金公司通常拥有百人级投研团队和全行业覆盖能力,而私募的研究团队规模普遍只有10~30人,而在交易执行和风控体系方面,公募基金的智能交易系统和多层风控体系是业绩稳定的重要支撑。头部公募的算法交易系统可实现毫秒级订单执行,且风控系统能实时监测持仓集中度、流动性风险等指标。而“平台依赖现象在公募‘奔私’经理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在他们从公募转向私募的初期,这种依赖往往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总的来说,大型公募公司往往为其基金经理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从专业的投研团队、先进的交易系统到强大的品牌背书与广泛的销售渠道,上述种种优势叠加,构成了明星基金经理过往高收益的‘安全垫’。”刘岩总结道。
也正因如此,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明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现象。刘有华提醒,部分投资者出于对公募时期业绩的追捧而盲目跟投,这种决策方式存在较大风险。需要认识到,公募与私募在运作机制上存在本质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基金经理的离任以及资管人才流动成为常态,这场“公奔私”浪潮并非单向迁徙,而是资管行业生态重构的开始。刘有华预测,这一趋势将促使两类机构各自优化发展路径:公募机构需要着力打造系统化的投研平台,通过工业化运作模式降低对个别基金经理的依赖;私募机构则需在保持策略灵活性的同时,重点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健全风险管理框架,并建立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专业品牌形象。他表示:“这种差异化发展将推动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形成更加健康、多元的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