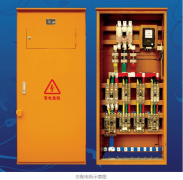这是一书中,
在满足了人们对食物、住所和安全的基本需求后,城市应具备包括让人们自由地生活、出行,在形态和系统方面尽力做到快乐最大化、困难最小化,为人们创造健康而非疾病等能力。
出版社: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随着城市的快速演进,大型城市综合体改变了城市尺度、孤立的大型建筑打破了城市肌理与街墙结构、封闭的高速通道和环路贯穿城区。凡此种种,造成了城市的社区如孤岛般被割裂,城市居民被规范在有限的活动空间,建筑与道路反而成为城市的“主人”。
“分散型城市是史上费用最昂贵、资源最密集、土地消耗最大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尽管人们在分散型城市上投入了很多,却没能将健康与幸福水平充分提升。
城市最大的成就与机遇,在于应加强人们与朋友、家人和陌生人之间的联系。如何将“人的尺度”贯彻于城市设计之中,跟随
何为城市的“分散”,其将给城市的居民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首先,理清“分散”的城市从何而来。
城市核心之外的住所,一度被称作“郊区”,而当郊区逐渐蔓延到城市边缘之外时,便有了“远郊”,当市中心的生意逐渐流向高速公路哺育出的商业区和大型商场时,这种新聚集区又被称作“边缘城市”。
如今的城市生活早已延伸为郊区、远郊和边缘城市共同构成的独特体系,改变了整个城市区域的运作方式。这一模式被
分散的城市带给人们的冲击在于社交难度的增加。
兰迪以较低的价格在美国加州斯托克顿南部的山屋地区购买了一套牧场式住宅,然而“优质”社区独栋住宅并没能为他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反而导致全家人工作需要经历长途通勤,开车穿过两座山脉、六个城市到湾区工作,往返超过120公里。
在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实际要告诉人们的道理在于,人们对找回钱包的信心与实际丢失及归还率基本无关,而更有意思的结论为,多数人对钱包问题的回答与他们的社交质量和频率有极大关系。
因为一旦人们失去了积极的社交,与周围人的信任纽带就不太能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几乎打不了照面的邻居,独栋山屋带来的疏离感……让兰迪失去对周围邻里的信心,在他看来,如果碰巧在街上丢了钱包,“那就再也找不到了”。
基于此,
此外,“社交互动潜力”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结论显示,在美国特大城市中,社交互动潜力面临的最大阻碍就是分散化,城市距离不仅限制了见面时间,实际上也改变了社交网络的形状和质量。
无论是聚会后向四面八方延伸散开的“朋友网”,亦或者是日益形成的社交孤岛导致的诸多社交网络薄弱社区,以及因此而从小受通勤影响的孩子所为此付出的代价,都反映着远途通勤带给人们的困境。“有时要经过整整一代人,人们才能看到在高速公路间奔波的损失。”
这也提示着人们,汽车作为如今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事实上,相当饱和的车辆数量背后,折射出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汽车本身未能提供给人们它本可提供的速度与自由体验,其力量被城市系统中和掉了。
例如,豪车、跑车仍能提升开车人的地位感,可一旦被其他汽车包围,它的力量就不起作用了。而利用汽车进行长途通勤的人们也在忍受着除了拥堵、路怒以及长时间驾驶以外的“社交窘境”。
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改善长途通勤者的“上下班路”体验,同时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汽车本应该带来的速度与自由体验?
不可否认,作为衡量城市空间辐射范围、交通便捷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勤时间对于居民感知城市交通服务水平和自身的幸福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显示,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中76%的通勤者45分钟以内可达。但仍然有超过1400万人单程通勤时长超过60分钟,承受极端通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5公里以内通勤比重的“幸福通勤”。
随着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的郊区和边缘地带不断扩充着“新城市人”,他们很大程度上成为极端通勤者的一部分。
如何让选择不同通勤方式的人都能够在城市里尽可能多地享受到自在,经济学家埃里克·布里顿认为,只有减少接驳的困难和阻碍,公共交通才可能提速,更接近自驾。
在上个世纪的巴黎,市民必须买5张不同的票才能横穿巴黎市中心,因此人们患有公交“出行焦虑”,几乎无人乘坐公共汽车,巴黎甚至开始考虑停止这项服务。
幸亏“橙色卡”适时推出,凭借这张集身份证与地铁票于一体的卡,在支付月度费用后,人们可以在当月无限次乘坐巴黎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免去了排队买票、搜找零钱以及忍受售票员白眼的烦恼,一年内,巴黎的公交客运量上升了40%。
同样,电车城市的开发也为如今轻轨或地铁规划提供了思路。
以伦敦为例,自从地铁站施行“进站倒计时”后,人们表示感觉等待时间缩短了1/4。倒计时也提升了人们的夜间乘车安全感,部分原因在于它增加了人对交通系统的信心。如今,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设施,却对当时的乘客有着强力的心理影响,“只要能看到实时到站数据,乘客就会更淡定,掌控感也更强。”
在纽约,也有类似的举措。列车站台上安装的显示到达时间的LED屏,不仅让乘客探出身子到轨道上方张望的危险可能性降低,也让人们对于是否走上街头步行或者招出租的决策更加有判断力,离经济学家描述的理性且信息充分的行动者,似乎又更近了一点儿。
城市能塑造人们的出行方式,人们的出行方式也能够反过来塑形城市。
以“世界自行车之都”哥本哈根为例,在汽车时代最初的几十年里,很多丹麦人曾一度放弃了以往的代步工具——自行车,更多人选择拥抱汽车,然而随后带来的却是持续的拥堵和能源危机,反而加剧了大众对以汽车为中心的道路设计的抵触。
呼吁之下,上世纪80年代,分离型自行车道应运而生,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建立起了一道低矮路沿,彻底隔开了两者。
自行车专用信号灯可以让骑车人比开车人多4秒额外时间起步;按照较快骑车速度调整的信号灯系统能让时速20公里的骑车人一路绿灯畅通地穿行城市间……
数据显示,现如今的哥本哈根拥有自行车数量比市民人数还要多。这并不是因为哥本哈根人天生爱骑车,
骑车通勤的人多了,如何平衡汽车、自行车、公共汽车和行人各自使用有限共享资源的权利?
之后,哥本哈根便有了类似如今国内大城市街道的普遍设计:为公交车建立专用车道,将通勤的小汽车分流到其他更宽的主干道,腾出来的空间用来加宽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哥本哈根的新标准是“交谈用自行车基础设施”,就是让车道宽到允许两人并排骑车聊天,让通勤更像社交活动一点。
和哥本哈根一样,共享单车也“重塑”了巴黎的交通体系。巴黎是第一座将公用自行车纳入交通系统的城市,共享单车为愿意分享空间和工具的人提供了新的自由,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共享单车的使用。2011年,巴黎进一步整合了共享汽车与地区公共交通,推出了共享电动汽车系统。
一座城市如果只为单一种出行方式设计道路,那么这条路上就会全是以这种方式出行的人。在本书中,
尽管一些城市的设计往往让步行和骑行既不舒服也不安全。而为什么速度慢、费力多的出行方式反而比开车更令人满足?
书中给出了解释,“部分答案就藏在人类的基本生理之中。我们生而为‘动’:不是被‘动’,而是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前行。我们的祖先已经行走了400万年。”